(来源:《语言文字周报》2018年12月26日第4版)
作者:宋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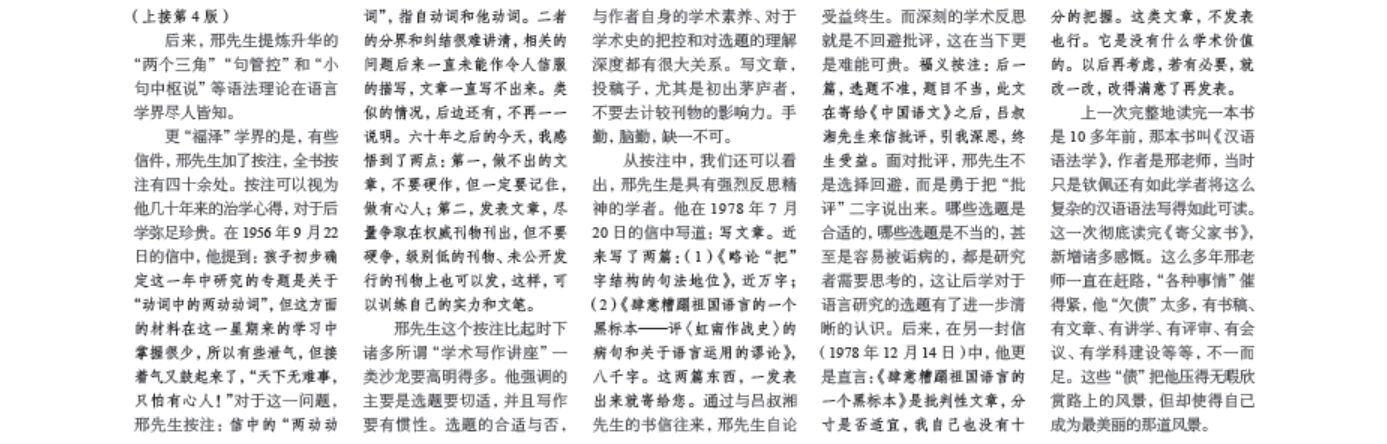
《寄父家书》(商务印书馆,2018年5月出版)收录了邢福义先生1955年至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40余封家信。邢先生,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,1935年6月30日出生于海南岛南部偏西的黄流乡,大专学历,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,与黎锦熙、王力、吕叔湘、朱德熙、胡裕树、张斌、陆俭明等人并称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。
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,物质上普遍贫瘠,但“小目标”让邢先生充满了前行的动力,他在1962年3月21日的信中写到:“走不尽的路,读不完的书。”古来有成就的学者,都懂得读书的艰苦性,需要极大的毅力。他们之所以有成就,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探索。儿还年轻,知识上又是“先天不足”,以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来要求自己,也许是过于轻狂,但,儿实在有这种雄心。
古之立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据邢先生自述,我从小就懂得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的道理,懂得“立志”之重要。很自然地,到琼台师范读图音体专师班时,“立志”要成为画家;到华中师院中文系读中文专修科时,“立志”要成为作家。直到留校担任现代汉语专业助教,确定了自己将终生跟这一专业打交道,便“立志”成为汉语语法学家。
随着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变化,邢先生与时俱“变”地将“小目标”一步步锁定为“汉语语法学家”。为此,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。据我了解,邢先生对于读书是不拘一格的,在桂子山语言所有一个两百平方米左右的资料室,古今中外的语言学资料一应俱全,那既是邢先生为语言所积攒的家底,也是他读书广博的印证。如果说在专业著作中的徜徉会得到最新的知识储备的话,那么,在文学作品中的睥睨则会为学术研究寻找到灵感。他和我们说,最爱读的作品是金庸小说,并自比为老顽童周伯通。每看到邢先生的研究成果,最愿意看的就是他的语言材料,看看他是怎样将文学与语言学“左右互博”的。他毫无保留地将“互博术”传授给学生,告诉学生读书要思考,写文章更是要做到“看得懂,信得过,用得上”。他在《光明日报》(2017年11月5日)对这九字诀做出了生动阐释。“九字诀”反映了我们的追求。但是,任何事情,要做到完美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能尽力为之,坚持再坚持。借用苏轼的话:“守其初心,始终不变!”
践迹入室时,邢先生的很多做法让我们做学生的备感温暖,但为何如此,不得而知,终于在《寄父家书》中,找到了答案。在他的自述中,记录着高庆赐教授对他说的一段话,1976年,我写成了论文《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》,他(高庆赐教授)大加赞赏。他说:“福义啊,看了你的文章,我觉得我都不会写文章了!”我知道,先生这是在鼓励我。
有师如此,邢先生就是这样把赏识教育的理念薪火相传,即使是对学生的批评,也可以做到让人觉得不那么刺耳。记得读博士时,每一次和先生研究论文大纲,先生都有备而来,有感而发,给我一一指出大纲的问题所在。我提交的第二份大纲,先生这样说,“你这个提纲可以做毕业论文,而且我相信可以做得很精彩,但我有三个建议……。”当时,我把最尖端的(包括技术难度非常高)的神经语言学、最时髦的认知语言学的一些想法都写在了大纲里,也确实想用三年的时间来攻坚,但不知里面的水有多深。先生说的“精彩”,现在想来当是一种批评,只不过先生照顾我的面子,没有说破而已,“精彩”意味着华而不实,意味着空中楼阁,当语言事实都没描写清楚时,“精彩”是不足取的。
任何研究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。邢先生对研究方法的重视,可以上升到方法论高度。从《寄父家书》所见,他早就有意识地在正确的研究方法指导下研究语言事实。在1961年1月13日的信中这样记载:一方面,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,写出了几篇文稿,其中,关于捍卫语言研究中的实践性原则,是全系的科研重点项目之一。另一方面,在具体的学习研究中,能够注意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。儿以为,已经写出的关于“们”和表数词语的并用,关于“A不AB”发问式,都是是在充分占有材料(收集材料的时间不下一年)的基础上,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影响下写出来的。
语言研究向来讲究对于语言事实的获取,这就是信中所谓的“实践性原则”。黎锦熙、王力等诸多学者都强调“例不十,法不立;例外不十,法不破”。有了语言材料后,需要用历时爬梳,同时需要辩证观测,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结论。其实,改革开放初期的语言学界对于语言研究方法格外重视。1984年11月8日的信中记录他去南开大学讲学的事情:南开是全国著名重点大学,排在中山大学前边。这次共请了四个中年学者去讲学,两个是北京大学的,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,再一个就是我。内容,都是讲“语法研究方法”。真是“四仙”过海,各显神通。
后来,邢先生提炼升华的“两个三角”、“句管控”和“小句中枢说”等语法理论在语言学界尽人皆知。
更“福泽”学界的是,有些信件,邢先生加了按注,全书按注有四十余处。按注可以视为他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,对于后学尤其弥足珍贵。在1956年9月22日的信中,他提到:孩子初步确定这一年中研究的专题是关于“动词中的两动动词”,但这方面的材料在这一星期来的学习中掌握很少,所以有些泄气,但接着气又鼓起来了,“天下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!”对于这一问题,邢先生按注:信中的“两动动词”,指自动词和他动词。二者的分界和纠结很难讲清,相关的问题后来一直未能作令人信服的描写,文章一直写不出来。类似的情况,后边还有,不再一一说明。六十年之后的今天,我感悟到了两点:第一,做不出的文章,不要硬作,但一定要记住,做有心人;第二,发表文章,尽量争取在权威刊物刊出,但不要硬争,级别低的刊物、未公开发行的刊物上也可以发,这样,可以训练自己的实力和文笔。
邢先生这个按注比起时下诸多所谓“学术写作讲座”一类沙龙要高明得多。他强调的主要是选题要切适,并且写作要有惯性。选题的合适与否,与作者自身的学术素养、对于学术史的把控和对选题的理解深度都有很大关系。写文章,投稿子,尤其是对初出茅庐者,不要去计较刊物的影响力。手勤,脑勤缺一不可。
从按注中,我们还可以看出,邢先生是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学者。他在1978年7月20日的信中写到:写文章。近来写了两篇:(1)《略论“把”字结构的句法地位》,近万字;(2)《肆意糟蹋祖国语言的一个黑标本——评(虹南作战史)的病句和关于语言运用的谬论》,八千字。这两篇东西,一发表出来就寄给您。通过与吕叔湘先生的书信往来,邢先生自论受益终生。而深刻的学术反思就是不回避批评,这在当下更是难能可贵。福义按注:后一篇,选题不准,题目不当,此文在寄给《中国语文》之后,吕叔湘先生来信批评,引我深思,终生受益。面对批评,邢先生不是选择回避,而是勇于把“批评”二字说出来。哪些选题是合适的,哪些选题是不当的,甚至是容易被诟病的,都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,这让后学对于语言研究的选题有了进一步清晰的认识。后来,在另一封信中(1978年12月14日),他更是直言:《肆意糟蹋祖国语言的一个黑标本》是批判性文章,分寸是否适宜,我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。这类文章,不发表也行。它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。以后再考虑,若有必要,就改一改,改得满意了再发表。
上一次完整地读完一本书是10多年前,那本书叫《汉语语法学》,作者是邢老师,当时只是钦佩还有如此学者将这么复杂的汉语语法写得如此可读。这一次彻底读完《寄父家书》,新增诸多感慨,这么多年邢老师一直在赶路,“各种事情”催得紧,他“欠债”太多,有书稿、有文章、有讲学、有评审、有会议、有学科建设等等不一而足,这些“债”把他压得无暇欣赏路上的风景,但同时也使得自己成为了最美丽的那道风景。